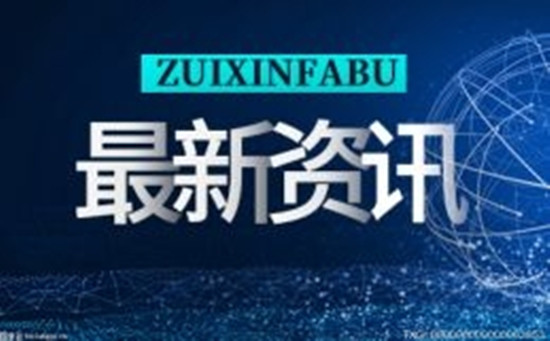北京的秋天有两大特色,一是景色美,层林尽然,秋风飒飒,在外面溜达甭提多舒服,二是时间短,凉爽宜人的日子总是那么短暂,转眼就入冬。那么在转瞬即逝的秋天里有哪些值得体验的事物呢?
后浪新书《我们的日子》里按四季顺序分享了在不同时节值得体验的小事,其中关于美食部分最淳朴动人。推荐书中以下这些食物,简简单单,但秋天吃起来就非常有幸福感:
 (资料图片)
(资料图片)
盐 水 煮 花 生
老北京的范围比现在的北京可小多了,所谓“内九外七皇城四”,说的就是北京内城有九个城门楼子,外城有七个城门楼,“皇城四”是说皇城东西南北有四个门楼,即东安门、西安门、天安门、地安门。这就是老北京的范围,其实就是现在的二环以内这么一小块地儿。出了二环就是农村了,一望无边的都是庄稼地,农民生产出的粮食瓜果蔬菜运到城里很方便,路程近,推车挎篮都不是事儿,走街串巷吆喝卖的也就多了。所以当时北京城里吃的都是时令农产品,什么季节吃什么食物,久而久之也就成了生活习惯。
秋天是收获的季节,大量的新鲜的农产品由农民肩挑车载涌入了城,城里人就有了口福。北京郊区盛产花生,秋天花生成熟了,农民从地里刨出花生,就把其中一部分加工成熟食,如炒花生、煮花生等,这样就好卖出,可以多挣些钱。就拿这煮花生来说吧,先要把新鲜花生用清水把上面的泥土洗干净,然后把每个花生都在上沿边儿的地方捏开一个裂口,为的是好入味儿。随后把开口的花生倒入灶上的大柴锅,加水,用柴火烧开,然后放入花椒、大料、八角、桂皮和大盐粒,开锅二十多分钟,最后放入少量的白胡椒粉和陈醋来提味儿,这一锅盐煮花生就齐活了。
煮是煮好了,但不能立刻去卖,必须捞出来放到大瓷盆里,在五香的盐水汤汁浸泡一夜,让每粒花生充分入味儿。第二天一早就可以捞出放在柳条筐中,挑担或推车进城串胡同吆喝:“五香咸落花生!”“咸花生哎咸花生,五香咸花生!”“好香的下酒菜哎!”
农民在加工花生的过程中投入了时间、劳力、辅料等,必然就提高了花生的售价,一斤煮花生,可比生花生加一倍或更多的价格卖出,农民就是靠勤劳挣一点儿辛苦钱。那会儿我们家里有时也买生花生自己煮,但总感到味道不如卖的好吃,听奶奶说是因为农民用的是大柴锅,烧的是灶火,煮出的东西都有香味儿,也可能吧。
爆 肚 儿
入秋了,又下了两场雨,熬过酷暑的北京可算凉快些了。这时,最能勾起北京人食欲的,莫过于“爆肚儿”。“爆肚儿”是老北京著名的小吃,好吃、便宜,当主菜、佐小酒儿都可以。旧时京城除了街头小饭馆儿常备,更有专营此物,货真价实,味鲜汤美的几家响当当的字号,像在“爆肚”后冠以姓氏的就有王、苑、冯、满、张等若干家,有的至今还门庭若市。
“爆肚儿”的“肚儿”就是牛和羊的胃,牛羊都是反刍动物,所以有四个胃,在做“爆肚儿”的食材时,就分得很详细了。先说牛肚吧,它分四个部分:肚仁、厚头、百叶、百叶尖。羊肚儿分的就更细了,有九个部位:肚仁、散丹、肚领、蘑菇头、肚丝儿、肚板儿、食信、蘑菇、葫芦。分这么细,是因为各部位的价格、口感,爆的火候儿、时间是不一样的。
“爆肚儿”的技艺有三绝,一是选料要精,二是刀法要好,最重要的是其三 —全在“爆”字上见功夫。爆肚要用大锅,水量得足,像爆散丹用五秒钟;肚板儿七秒;肚领、肚葫芦、肚蘑菇八秒。如果过了火候儿,就会又老又硬嚼不动了。
取材的羊,好的是张家口北的绵羊,胃又肥又大,最好当天宰杀,要新鲜,刀功要好,切得薄而细。吃“爆肚儿”还需要蘸佐料,这可是各家的绝活儿,这些名店都有自己的配方,秘不告人。虽不知精华详情,但主要的材料是芝麻酱、香油、豆腐乳、虾油、酱油、 韭菜花儿等,在食客吃时自己加葱花、香菜、蒜汁儿、辣椒油,用筷子把这些搅拌均匀,吃“爆肚儿”时讲究用筷子一次夹一块,从碗底往上蘸,这样肚儿上托着葱花、香菜末等调料一块儿送入口中。入口后要用后槽牙,嚼出“齿感”,嘎吱嘎吱的,这才叫吃爆肚的行家里手呢!再喝上一口二锅头,那真是够味儿。与之相配的主食是芝麻酱烧饼,最后来碗羊杂汤,北京人称之为“溜缝儿”。一顿平民百姓吃得起、吃得有滋有味的一顿饭就齐活了。
小时候家住得离什刹海不远,所以跟着大人我到什刹海边儿的“爆肚张”吃过几次。听说他家是一八八三年就在这里经营爆肚生意了,最初祖上是从山东到北京,拜在一位老人门下学爆肚手艺,后来在什刹海边上支锅,艰难地经营这个小生意,再后来又在烟袋斜街“义合轩”大酒缸门前摆摊。“大酒缸”是过去酒铺的别号,因为店内有直径一米左右的储酒大缸,下面一截儿埋地下,缸的上面盖一个大圆桌面,就当桌子用,酒客围坐在四周饮酒聊天。酒客不仅喝酒还得吃下酒菜,其中爆肚儿就是最好的佐酒吃食了。要吃的时候让店伙计到门外爆肚张摊儿上,点名要爆肚儿的哪个部位,立马选料切丝,配上佐料,端进大酒缸放在食客面前,供客人享用。爆肚儿摊儿和大酒缸是相傍依存的。
老北京这些名小吃、名店能传世远扬,都是口碑好,选料精,货真价实,做工地道,所以买卖才能越做越红火。像“爆肚张”至今已第四代了,从祖上的摆摊儿到现已是有六十多平方米,古香古色的大店铺了,也成了什刹海著名的美食之一,是我们北京名小吃的传世的一个缩影。因为爆肚是热吃,所以喜欢这口儿的北京人,常以之作为立秋后补夏的首选几样吃食之一。“爆肚儿”性温养胃,据说可治胃病,素有“要吃秋,有爆肚儿”之说。
入 秋 吃 螃 蟹
每当农历七月底八月初,暑气渐退,金风送爽, 人们从酷热中熬过来,心情大好,胃口大开。秋天可算盼到了,这是收获的季节,老北京历来有“入秋尝秋鲜”一说,而螃蟹正是首选。现如今一提吃螃蟹,就是阳澄湖大闸蟹,我小时候可从没听说过什么“大闸蟹”,只知螃蟹分海蟹和河蟹两大类,而北京能吃到的基本都是河蟹。
北京卖鱼虾的商铺这季节都兼营此物,而且都打着 “胜芳螃蟹”的旗号,当然其中很多是冒牌货。天津郊区沼泽地胜芳镇盛产螃蟹有名,运到京城,大饭庄先挑肥大的、活力十足的上等“帽儿货”,二等的再由北京的大鱼行筛选,像西四牌楼东南角的西四鱼行,每年都进大量的胜芳螃蟹,剩下又小又瘦的次品,就由小贩低价买入。那时北京郊区的河湖道汊特别多,像京东的温榆河、潮白河,京东南的马驹桥一带,都盛产螃蟹,味道不亚于胜芳螃蟹,小贩也会到这些地方趸货,到城里进胡同叫卖。
卖螃蟹的小贩都是肩挑竹篓,头戴草帽,腰系围裙,边走边吆喝:“约[yāo]螃蟹来,大螃蟹!尖脐的肥喽!”“哎嗨哎,大活螃蟹嘞哎!”到农历八月,吆喝的时候就把“尖脐”改成“团脐”,其他的词不变。胡同四合院里的奶奶大妈们听到吆喝声出来问价,看货,挑选。小贩用又长又细又有韧性的马莲草叶子给捆好,一只一只上下连成串,螃蟹还吐着沬子。买回来以后,要把螃蟹放入大盆清水中,让它吐吐肚内杂物。
到晩上快吃晚饭时,螃蟹捆着草绳就放入蒸锅大火蒸熟,掀开锅盖,青灰色的螃蟹变成红红的了, 十分鲜艳,蟹香扑面而来。趁热吃,尖脐掀开蟹壳,白色半透明的蟹膏就露出来了。如果是团脐,露出是橘红色的蟹黄。我尤其喜欢吃蟹黄,蘸上鲜姜泡米醋的汁液祛寒提味。姜醋和蟹黄的味道相融合,口中感受此美味,真是一大享受。大人们往往会烫一斤花雕黄酒,大口吃蟹,大碗喝酒,如果正逢八月十五,全家团聚,那真是美食醉人,尽享天伦之乐了。这种在家吃螃蟹是最经济实惠的,所以老北京百姓大多居家吃蟹。
当然除了美食,秋天还有很多值得做的事,《我们的日子》还列举了诸如节日如何庆祝以及各个时节受欢迎的小玩意儿等等,跟随书中的推荐,给这个秋天多一点仪式感。